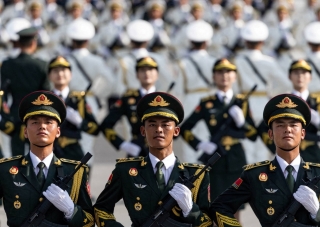老夫子穿不稱身唐裝衫的老派形象深入人心,作者王家禧卻不是「八股佬」,反而是位潮爆的「虎爸」:11歲駕駛電單車、18歲玩爵士樂扮嬉皮士,順手拈來長子的名字作筆名,卻不喜子承父業;兒子個個學有所成,可是最後卻全部承繼了他的衣砵……。
撰文:馬如風 本刊特約記者
這一天風和日麗,充滿笑聲、眼淚,又帶點淡淡愁緒,追憶逝水年代。
中午到蘇富比藝術空間捧王澤的場,欣賞「老夫子手稿展」,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湧現;晚上到葵青劇院看韋然的創作—— 一齣有關王司馬與牛仔的原創音樂劇《飛行棋》,描述漫畫與現實那一代父親為口奔馳的戲中戲,笑中催淚。不同的漫畫,都是陪伴我成長的重要文化icon。人生如戲,戲如人生,作者背後兩代父子情,原來比漫畫更令人動容。
本土漫畫家代表 寧自毀衣砵
「好好先生」王司馬離開了我們20年,43歲英年早逝,堅持畫到斷氣,漫畫主角牛仔與契爺的關係温暖人心;現實中,作者遺下了三個兒子和全家一起到美國迪士尼樂園的夢,怎不教人唏噓神傷?王澤代替了筆名王澤的父親王家禧主理有51年歷史的《老夫子》事業,聊起定居於美國洛杉磯九秩高齡王老先生的點滴,才知道這位老夫子潮爸許多鮮為人知的妙人妙事。
「爸爸講到明不希望我們畫畫,記得當年我到美國升學,父親送機時語重心長的對我說:『讀不成書不要緊,但寧願你學修車也千萬別要畫畫。』」這位本土一代漫畫家的大兒子得到父親苦口婆心的囑咐,縱然《老夫子》當年已大紅大紫,但父親卑微的期許竟然是自毀衣缽。更諷刺的是,6個遺傳了他美術細胞的兒子都逆他的意。王澤笑說:「好似傳染病般,我們兄弟有醫學院畢業或者讀電子工程的,但最後全變成漫畫家或動畫家,哈哈!」1950年出生的大哥王澤,曾任教美國費城藝術大學建築系和台北實踐大學的建築系。從王家禧對兒子的期望看到,執筆生涯,何其辛勞?
北洋軍閥後代 一輩子拿筆桿
王澤說,小時候兄弟們都以為所有小朋友的爸爸都是畫畫為生的,「畫畫」變成了工作的代名詞。王澤憶述小時候老師問他父親做什麼職業?他答道:「畫公仔。」外界又可能理解一枝筆桿何以撑起一頭家?「記得我小學四年級有同學看《老夫子》被老師沒收,老師很生氣叫我們不要荒廢學業看漫畫,成班同學立刻望住我。」
1924年天津出生的王家禧,父親是北洋軍閥、曾任直隸省長的王承斌。1944年從北京輔仁大學西方藝術系畢業,曾在天津任美術工作。1956年移居香港,沒有想過繪畫漫畫可以維生,並成為終身職業。當然他也沒有想過《老夫子》會成為華人漫畫中出版年期最久,讀者層面最為廣泛的紀錄保持者,《老夫子》漫畫從1964年在香港首度發行,各類單行本連續發行超過半個世紀,其間也創作過多部影視作品,風靡整個華人社會。
成功的背後要消磨過多少志氣,又可足為外人道?
秦先生無奈際遇 屬夫子自道
王澤記得,父親1956年從天津移居至香港,不停找工作,前路茫茫。「《老夫子》裏面的秦先生就是他的原型,紅咖啡色布鞋,不停找工作,記得有一則漫畫講秦先生在街上被石頭絆倒,他踢那塊石頭,結果是自己的腳痛,石頭根本不會痛,反映了他當時的無奈。」不久,王家禧便在香港天主教《樂鋒報》繪畫插畫與長篇故事近10年。業餘時,他在香港各報章雜誌以「萌芽」等十幾種筆名發表漫畫。「印象最深是1957年,我父親第一次投稿《星島晚報》每周四的漫畫版,他緊張地買報紙看,沒有刊登,好失望;第二次再投稿,還是沒有;第三次投稿,終於登了出來,他興奮得要命。」從此,王家禧首次以長子王澤之名為筆名,畫老夫子漫畫,慢慢為人所熟悉。
「為了應付排山倒海的工作量,父親經常要執筆到深宵,有次父親見我也是畫到半夜兩點,正想問我為何未睡?當他見到我在畫漫畫送給女孩子時,他沒哼一句話,面帶理解神色便回房休息。」王家禧比誰都明白,一個畫師的生理時鐘,執筆揾食的人黃金創作時段,有別於一般朝九晚六的辦公室上班族。
出書食不甘味 賣斷市鬆口氣
1964年7月的一個暑天,王澤記得從未見過父親如此焦慮,那天是關鍵的一天,原來是老夫子正式成書的大日子。「是吳興記首次答允出版《老夫子漫畫》,出版日父親在家裏踱來踱去,食而無味,直到吳興記告知第一期全部賣光了,父親才鬆一口氣。出書的意義非常重大,代表從此擁有自己的出版平台,個人的完全自由。」之後,王家禧的創作包括有《水虎傳》、《猛鬼廟》、《古老村》、《狐狸仙》等中長篇及短篇漫畫,後來甚至登上大銀幕。
老夫子的形象也深入了華人社會,水墨紙本作品帶有強烈的時代感及生活感,角色造型生動,人物表情豐富,也與時並進,當中涉及許多草根故事和時代精神,令香港人特別容易產生共鳴。
事實上,穿着滑稽而不稱身唐裝的老夫子這位主角背後,其實蘊藏許多對現代事物甚至未來的投射,例如漫畫中經常出現飛碟和外星生物,故事精神也非常當代。王澤透露,王家禧絕非一位八股思維的守舊老爸,反而是一位前衛新潮的「虎爸」,《老夫子》自然是當代藝術的一種表現。
王澤說父親前衛,有何真憑實據?
奇裝異服飛仔 原是自我寫照
「電單車與釣魚是父親兩大嗜好,所以你會見到這兩種題材經常在《老夫子》漫畫出現,他細心觀察社會發生的事件,搬到紙上,好似『飛仔』現象、披頭四、打劫熱潮、乒乓外交、美國人登陸月球,統統出現在漫畫裏,並加入了王式想像和幽默元素。」王澤直指,老夫子的舊中國裝束,其實是父親反傳統的象徵。「我父親是個反傳統的人,11歲駕駛哈利電單車(Harley Davidson),17、18歲已有自己的爵士樂隊,還會留長鬍鬚穿着奇裝異服,漫畫裏最『潮』的元素其實是他的自我描繪。」回歸平淡的王老先生如今在美國退休享清福也是不愁寂寞,最大嗜好仍然是畫漫畫、釣魚及造陶器。
老畫家退而不休 改當「判官」
「父親已由漫畫家變成漫畫判官,他會審批我畫的漫畫,家中經常放着一疊疊貼滿黃色小紙條的漫畫畫稿,都是父親要我修改的記號和指示,每條線都一絲不苟,他對《老夫子漫畫》仍然放不下;離不開陪伴了自己逾半個世紀的『老友』。」王澤透露,老父在20年前,即1994年已因手震減少繪畫《老夫子漫畫》,由一星期畫一張,變成一個月畫一張,但仍堅持每期自己畫漫畫封面。「後來他患上白內障,見他畫彩色封面時填色總是出了界而不自知,我也感到心痛,於是1998年他便完全封筆,轉行當起了我的判官。」王家禧昔日一直用毛筆畫老夫子,也有用龜筆(繪畫用小毛筆)畫,喜歡把搞笑元素放在漫畫裏,表達他的樂天性格。「他的靈感來自生活,再加上60至80年代最『潮』的元素,創作已不勝應用。」
《老夫子》的確帶給我許多快樂的童年回憶,看到展覽一幀《三位一體》手稿尤其開懷:老夫子、大番薯、秦先生看電影為了省錢只買一張戲票,三人「疊羅漢」坐一個位子;或者講賊仔打劫、老夫子在西餐廳「鋸扒」吃得手忙腳亂,也是表達出六、七十年代香港不少家庭生活艱難,慳得就慳、中西文化衝擊的現象,這是八、九十後物質豐富的新生代難以理解的,也是我認為《老夫子》最有價值的「草根俗文化」。
諷刺拿人開刀 幽默自甘小丑
老夫子擁有樂天的阿Q精神,正是王家禧骨髓裏煶煉出來。「記得考試常常包尾的弟弟有次派成績表後,父親二話不說帶着弟弟坐上他最愛的電單車絕塵而去,回來後弟弟手裏拿着一大盒玩具車,父親比弟弟還興奮大聲說:「我個仔考尾二,終於他強過別人了!」這就是王家禧,《老夫子》漫畫的確像是他的樂天日子,上一代香港人就是有這種苦中作樂的獅子山精神。據王澤的理解是:「諷刺漫畫是拿別人開刀,幽默漫畫是把自己表演成小丑。」
不過,《老夫子》縱使揚名世界,但很多人對漫畫還是有盲點。「亞洲人對於漫畫和插圖,都有一種歧視和看不起,認為是藝術領域裏最後的小尾巴。其實漫畫家和作家、小說家的性質是一樣的,只不過用的語言是線條,它體現的仍是創作者的思考內涵。」他認為, 如何衝破框框的限制, 是漫畫家的工夫。四格漫畫代表了說故事的基本技巧——起承轉合,「眾所周知, 第四格是所謂的爆笑點(punchline),但其實好的四格漫畫,第三格很重要,因為這格要將故事轉接到結局,又要令讀者猜不到後續。」王澤說,《老夫子》成功在於夠簡單方便,「四格或六格漫畫很快便看完,隨便翻開一頁都可以看,最適合生活緊張、壓力大的城市人閱讀。」
老夫子的記憶,等於王家禧的記憶,也代表一代人的記憶:香港曾經有過一個樸素、對前景有美好期望而並非互相指摘的年代,它苦中作樂、得意忘形、先苦後甜,最重要的是:耐人尋味。